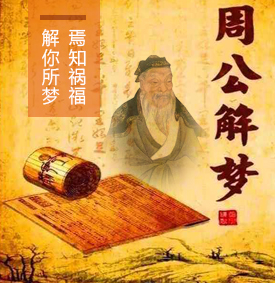我所理解的郑晓江教授
今年2月21日晚,忽然接到景海峰兄发来的一则手机短信,打开一看:《惊闻郑晓江逝,寄言以悼之》“傅子倡导生死学,内陆和声有晓江。死亡尊严惊天跳,从此世间无解人。”“人生难言生死事,生死事大总怅恍。绵绵若存当敬畏,原始反终归无言。”是写给江西师范大学郑晓江教授的。怎么会这样?我心里想着,赶紧给在江西师大与晓江同事的学生打电话。学生证实这是真事,说是2月17日上午7点左右,从18楼跳下去的。学生很难受,我听得出来,声音很哀戚。
2月22日,又接到友人王兴国教授的短信:“南昌有个郑晓江,勤奋治学有遗章。平生最擅死亡学,不知死亡向己张。……”心里愈加不能平静,上网再度查询,还是老样子:搞生命教育的教授,无缘由的自我了断,引发深思。如此之类的拙劣新闻报导,瞬间挡住视线。我看不下去,关掉了。
对于晓江的离世,我很震惊,尤其是对这种离去的方式。我几乎没有想到,因为他一直很开朗,很敞亮。看来表面上豁达的人,心里的内在自决力更强大,来势也许更凶猛。
晓江与我虽是老相识,算是不错的朋友,但是没有心里上的特别深度的交流。他这个人在这方面一直封闭较严,好像不很愿意跟什么人特别深入地交心,从而成为彻彻底底的朋友。这可能是他对人的个体自尊的理解。
我们相识已有十余年,最初认识应该是在2000年秋天,我们一起参加在江西上饶召开的纪念朱子逝世8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会议是由时任上饶师范学院副校长的才子型学者吴长庚教授发起并主持安排的。那时,晓江很牛,一般年轻的学者不容易得到机会靠近他。我们也只是认识了而已,只是感觉他人很聪明,学问做得不错,但是有点“傲慢”。
在那一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认识了名声很大的蔡仁厚和李明辉两位台湾教授,他们都与名噪一时的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有亲密瓜葛。不过在会场上他们都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跟新儒家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台湾退休女教师,给在场的所有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早就忘了她叫什么,但却永远忘不了她在讲话时的声音:“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也。’……”那个悠扬、那个婉转、那个和润、那个抑扬顿挫而又错落有致、轻重得体而又高低适中、清晰但不短促、浑厚但不浑浊、优长又不拖沓,那个使人完全可以忘记她在说什么,只是想听她不停地说下去的感觉,马上就会使人想起古人“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话语。人类的肉嗓子,真能发出天底下最美的声音,什么乐器都会望尘莫及、望洋兴叹。那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由人所发出来的最美的声音。
第二次见面后,我和晓江的关系开始正式拉近。那是一年后在湖北丹江口召开的一次儒家伦理之类的会议期间。
在那次会议的空闲时间里,晓江提着一架照相机,东拍西摄的,好像要去参加作品竞赛的摄影爱好者。他也给我拍了几张照片,但却一直没有给我。因为距离非常近,我这才看清,晓江矮胖,脖子很短,脸很阔厚,头很大,而且脑袋差不多像是直接长在肩膀上一样。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从大脑发出来的信息,能够在比别人短的时间内,传达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所以,他反映很快,人也相当聪明。
一天晚上,会议聚餐之后,一位韩国的学者忽然发起飙来,强硬地纠缠一位参会的江西女教师,说是要去找地方“快乐”。那场景,让人不由想起电影里日本兵见到中国女孩子的情形。当时这位老师跟一位湖北的女老师在一起,非常尴尬,又非常恐慌。湖北的老师几乎是在喊救助。刚好我走过来,帮她解了围。
因为这件事,那两位女老师很感激我,我觉得无所谓。这算不上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时我有一种心理,就是这里包含着中国学者的尊严!一个喝多了的外籍学者,不可以在中国的境内这样撒野!当然,我没有对他发怒,因为他是学者,又喝得太多,可能一时间理智不清醒。我也给他留足了尊严。
就是这位湖北的女教师,在此事发生前的一天,会议主持的参观丹江口水电站的旅行途中,看到我穿着一件很大的风衣,站在船头,被风吹拂的感觉,忽然说了一句:“太潇洒了,简直就是女性杀手!”晓江听到以后,哈哈大笑,并且在此后的各种场合,都拿这样的话语当着大家的面跟我开玩笑。从那以后,经常有人在各种见面的场合,叫我女性杀手,但意思却在传递过程中,有些走样了。能得到这样一个被当成“潇洒”象征的绰号,主要就应该归功于晓江教授,虽然发起人不是他,但他传播起来,似乎不遗余力,大家听起来也很好玩。但是那位女教师,从打那件事情以后,却再也不对我提起“女性杀手”这个词汇了。
会议要结束了,我和晓江都在武当山上买了几把宝剑作为留念。后来我们再见面时,还互相问起那几把剑是怎样带回去的。他说他藏起来,没有被火车站检查出来。我是被检查出来了,但是明白的告诉检查者说:这是开会买的纪念品。还说我是大学老师,并出示了身份证明。检查者就这样让我把两把剑带上了火车。那时节,社会上还知道信任老师是一种美德。现在连老师都没人信任了,大家不愿意相信任何人,只是机械地履行各种公务,麻木的看待所有从身边匆忙经过的各色行人。
两年之后,我和晓江在湖南郴州汝城县的周敦颐学术研讨会上再度见面。他依然提着一架照相机,四处拍照。
那次会议期间,地方组织者带我们来到一个温泉。农民们早已准备好用温泉煮熟的土鸡蛋,眼看着刚煮好的,每人一个。我拿了两个,还在窃窃私喜,不想晓江高兴地走过来,说他吃了两个,“真好吃,吃完我又拿了一个”。好家伙!他一个人干掉仨,我还以为只有我偷偷的多得了一个呢。
又两年,晓江和我在湖南永州道县的周敦颐会议上相见。在传说周敦颐悟出太极图的月岩洞里,晓江还是提着一架并不先进的普通照相机,我们一起仰头从洞底看天,天空一线,确实有点像上玄月或者下玄月。
那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晓江希望我能帮助他们在申报博士点上出点力。因为我当时已成功申请到了博士点,也就自然的成了向后任何申报博士点的可能的评审者。当然这种求我帮忙的话语,晓江是讲不出来的。因为他比我大几岁,又一直以为他在学术上也是大哥,不可轻易屈尊。于是就只能由李承贵跟我讲,承贵也不会轻易屈尊,虽然他比我年纪小。但是他会婉转,说笑嬉闹之间,就把意思表达出来了。其实这种话对于我来讲,是不用说的。如果他们的申报材料真的落在我手里,我是一定会尽量把最好的话语说出来的。不仅是因为关系不错,人家那一班人马也确实很厉害。当时他们南昌大学除了晓江和承贵以外,还有杨柱才、杨雪骋等,都是相当不错的学者。不久之后,承贵去了南京大学,南昌大学的力量减弱了,晓江似乎也与他所在的学校有些不协和,于是就到江西师范大学去了。再见面的时候,他就不断的跟我说,江西师大给了他很优厚的工作条件,每人一个办公室,连我在那里的学生也有。他甚至说:“老王,上我这来吧,我这里很舒服。不要在体制里跟着走了,太累。”
想不起是因为一件什么事情,一次我给晓江打电话,他在电话里跟我说:“老王,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学会做减法了,不要总是把各种负担和研究任务都往自己身上加,身体重要哇。”我觉得这样的话语里虽然有他的无奈,同时也有他的真实想法和对我的真心关爱。我感激晓江,开始用这样的口吻跟我讲话了。他已经深受体制之害,同时也因努力跟这种越来越冷酷无情、越来越令人生厌,同时也搞得大家越来越疲倦的申报、评估体制周旋得太累、太苦,他不想再这样走下去,他开始真正思考人生的道路问题了。于是他开设起生死学的课程来了。晓江对此很自得,也很自信。我想他的目的和用意都很明显,就是想告诉大家:珍惜生命比做什么样的学问、获得什么样的学术成果都更加重要。晓江是对的,但是这里本来就有属于他自己的无奈。他已经走不通申报基地、申报学位点、申报重点学科、申报各种级别的课题的道路。虽然他曾经走进去过,也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面对这种越来越使人疲惫不堪而且头晕目眩的体制,他终于走不下去了,也彻彻底底的不愿意再那样的跟着走下去。因为无论你多有多大本事,你总有跟不上的那一天、跟不起的那一天。任凭你身体再好,精力再旺盛,你也没有可能跟随这样一种不断增加对人的身心两面压力,变得越来越无聊,甚至越来越疯癫的申报、评价、审核体制走下去。人的身心的抗击打能力是有限的,任凭你怎么锻炼,你总还是人,你的肉体变不成大象和河马,你的心理变不成鳄鱼和乌龟。不会再生出那样强大的抗压力和耐久的忍受力。时下的这种体制,就像把青蛙放在锅里,慢慢加温一样。没有人不懂这个道理,但似乎并没有几个人比青蛙的智商高一些,都在不断的跟着走,没有抗争,也不想逃离。在这一点上,晓江是个例外,他确实比青蛙的智商高。仅就这一点,那些顶着博士、教授、博导、这个学者那个学者、这个带头人那个带头人的可怜的青蛙们,比起晓江学兄来,不仅是境界差得多,而且真的智商也差得多。晓江是杰出的!
晓江是杰出的。一开始从事理学研究的时候,他就是杰出的。当年晓江就喜欢他自称为“思想访古”的方式,四处活动,翻山越岭,寻访古代思想家的遗踪遗迹,同时穿梭在大自然的美妙风光中。回来之后,马上书写成文字。在寻访的过程中,晓江雅兴闲情,不断写些五言、七言的古诗发给我。不是糟蹋老朋友,他发给我的这些诗,实话实说,只能算是顺口溜。晓江或许并不缺乏这种对于诗歌和艺术的自知,不过他可能是觉得这种方式平白直接,所以才故作这种白乐天式的通俗表达。但是白乐天的表达形式是诗,晓江的表达,只是顺口溜。如果晓江还在,我永远都不会让他知道我的这种感觉,那样朋友会伤心。这几年,他至少给我发了不下三十首这样的顺口溜,我当然没有必要在这里展示这些,不过这个事实至少表明了晓江走过的地方之多,行动之勤和劳绩之深,他确实为了这种“思想访古”的事业,投入了非常多的心思和精力。
晓江的这种“思想访古”,跟我的“田野悟学”,其实相差不多。我也经常带研究生和本科生们下乡调查,深入大山丛林,寻访古代先哲的遗迹和行踪,借机诱导青年学生,慢慢激发他们对古代文化的热情。我的这种做法,一度被吴长庚戏称为“当代的周游列国”。不过我没有晓江本领大,他到哪里都有人接应,随行人员也因此少受了不少苦。我就没这个本事,只是一路苦行,经常“受困陈蔡”,好在没被当成“阳虎”,受到匡人的围攻。一次带着七、八个学生,几乎露宿武夷山下,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多了,店家又不肯降价收留。多亏吴长庚教授盛情邀请,安排全员在上饶师院吃了一顿美餐,要不然随行的孩子们都快饿昏了,真成了“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了”。要是到得那样的时刻,咱可没有老夫子的本事,“讲诵弦歌不竭”。还有一次,我与一位叫尹文汉的学生,两人一路踏着泥泞的山路,冒着风雪行进,钱快花光了,到得最后,只能按分按角的分钱,以保证各自都能回家过年。虽然如此,我们的情致依然很高,文汉还作了古诗,其中一句现在还记得,觉得写得不错,叫做“青山一夜尽白头”,那天湖南宁乡的那场的雪,下得着实够大的。
晓江的思想访古,本来走的就是通向体制外的道路,但那不是申报、评审和评估的大体制,而是学术研究本身的小体制。他不想拘泥于文本的研究,整天抱着几本书,说书里说了什么什么,然后再说别人理解的不对,再然后就是互相争论,甚至吵架。我跟兴国教授亲眼见过这样的情形:在一次重大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两位中国学者,脸红脖子粗地进行了一场不知道会给在场者一种什么样感觉的“学术争论”。其中一位发表自己对《老子》的看法,另一位则说“不同意他的看法”,这位竟然拍了桌子,大喊大叫地吼着:“上次在某个会议上,你就故意跟我过不去!”这位同样不依不饶:“你上次说的就不对,那一次我算是对你客气的”……相比来讲,晓江又杰出了。
这是晓江送我的书和他的题字。
晓江后来四出讲学,讲古代思想家,讲生死学,讲生命教育,气场不小,但多半都是在地市级城市的师范学院之类的小学校里。身居大城市的人们并不太关心他的创举和成就,以为那不过是他个人玩的“小把戏”。这就使得晓江想要得到正统学界中的名教授、名学者们的关注的祈望,自然成了泡影,他肯定感到失落了。体制内的“正统派教授们”,很多都觉得晓江脱离了自己的本行,似乎有点“不务正业”。其实,这也是那些没有勇气和能力走出体制的限制,走上晓江的自选式道路的人们的一种居高临下的自我安慰。一些体制内占据“正统”地位的专家学者们的误解,虽然都不会直接跟晓江表达,但是晓江并不迟钝,他应该感觉到了,他的心里肯定又添了一层阴影。为了摆脱这种阴影,晓江逢着熟悉的学界朋友,就故意运足神情,炫耀自己这种做法的畅快和所得的丰硕。我从他的表白里,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我理解他,我绝对是他的支持者。但是这不等于学界能够真正理解他,就像学界也不一定能够理解我一样。
晓江研究生死学,四处巡讲生命的意义,并不能简单的被看成是对傅伟勋教授创立生死学研究的大陆附和者。晓江可能在形上学的意义上赶不上傅伟勋教授,但是晓江面对大陆青年和社会人士,范围广大,目标明确,针对性强。这一点,绝不是只在书斋里谋划“学科体系”和“研究程序”的傅伟勋教授所能比拟。在生命教育这个环节上,晓江所获得的实际的成就,绝对远远超过傅伟勋!我今天敢说这样的话,也是因为刚刚说到的两个人,现在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为什么一提起外籍学者、港台学者,好像就比大陆学者强?为什么总好像大陆学者似乎只是在推广或者追随那些境外的学者?大陆学者怎么了?大陆学者面对的是比这些境外的学者们更加复杂、更加实际、更加真实的生存世界。他们不像境外的学者,可以轻松地关在书斋里,悠然自得的“研究”自己的学术,玩弄自己的“形上功夫”。当然,一些境外学者在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自然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也确实给了大陆学者很多有益的启发。但是大陆学者们的现世关怀和在现世中的艰难奋斗历程,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显然具有更加真切的现实意义。
2008年11月,在广东江门召开的陈白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晓江又和我见面了。晓江说他把王阳明的一句话读了“一百遍”,才读出里面的真正味道。显然,晓江在夸耀他读书明理的认真态度。其实以晓江的聪明、练达,如果想要对某句经典或者古训获得一种全新的理解,读上个三、四遍是可能的,根本不用读一百遍,也完全没有必要读一百遍。他为了说明他自己的崭新收获,经常说出这种故作艰难而辛苦的吓人话语。虽然他的这种展示或者提醒方式,未必使大家心里舒服,可他确实经常能说出一些惯常的材料里,还有惯常的学者们看不到的细腻的味道。在这方面,我曾受益于这位老朋友。他曾在讲说他所理解的周敦颐时,提出了“人生的政治化和政治的人生化”的说法。说很多人都把人生政治化了,以为人生就是为了当官,把人生的全部精力都押在了做官上面;而周敦颐则把政治人生化了,他做官只是人生的一个步骤、一种样式。不被政治捆绑,不作政治的奴隶,而是要努力使政治为人生服务。这大约就是他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我领会到了,也受了很大的启发。相比于某位挂着博士头衔,披着教授外衣的行政领导,跑到我的办公室来骂我的同事景海峰时说的:“作他妈什么学问,学问有他妈什么好做的”之类的话语,真给人一种一个是翡翠,一个是鼠粪的感觉。晓江虽然造作了一些,但是,他确实又杰出了一回。
当然,这位行政领导还算是坦率的,更多的领导们,却打着支持学术研究的旗号,让你无休止地去报项目、做课题、争基地、争学位点,然后,他好去上报成绩。拿这些可怜的读书人的繁重劳动,去充当自己的领导功绩;用这些“小知识分子”们本来已经所剩不多的心血,为自己的升官发财铺路奠基,涂红并染亮自己的顶戴花翎。
前不久,一位与我一样,跟晓江有较多交往的教授诚恳的对我说:“其实在晓江这件事出来之前,我也想自己做个了断了。太累、太烦、太没意思了,我现在什么课题也不作,什么奖项也不报。我只求讲好每一堂课,把我的全部人生体会,都当成课程的材料,就像广东人调制茶汤一样,作最大可能的充分准备,对得起学生,对得住自己。”他还说:“上课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是老师,我们最应该对得起的是学生。而且只因为学生,我们才成为老师,我们能成为合格的老师,都是在学生的渴望和刺激下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生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没有必要去对得住上边,只要对得住学生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跟着无聊的指挥棒走,受苦受累,摧残自己的身心,浪费自己的生命,使自己永远不得安宁。”
多好的老师,多好的话语呀!他们在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里都一样,给他们所在的时代留下希望。在任何时代里,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
对于自我了断,其实只要是自觉的人生,或者已经生出一定人生自觉性的人,差不多都有过类似的想法,只是深浅程度不同而已。只要环境的威逼到得一定程度,人是难以自持的。这一点不用去问心理医生,每个有一定自我意识的人,几乎都会有这种心理感觉。
在江门会议期间,主持人五邑大学的刘兴邦教授,特意安排大家参观了陈白沙和梁启超的故居,之后又参观了江门市的华侨广场。
这是两张当时跟晓江在江门市华侨广场拍摄的合照,前一张是华侨广场的正门。后一张是我跟晓江在广场边上休息时聊天的场景,被随行的学生偷拍了。偷拍者是现在中大读博即将毕业的陈椰。可能是因为我说得兴奋了,动作幅度太大,左手被照虚了。看晓江的表情和神态,多阳光!就在我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竟然意外发现了一段录像,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我讲说论文时的情形,也是陈椰偷拍的。当时晓江一直坐在我的身边,看我在那里比手画脚,听我在那里侃侃而谈。因为文档承载不下,所以无法安放在这里。
好像是2011年6月前后,一天晚上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他来深圳了,希望见一面。我说明早我请你吃早茶。其实我根本就不懂广东的早茶,只是知道这种吃法,可以拖延很长时间,便于聊天。而且他说上午十点在深大有一次生命哲学的讲座。我感到有些意外,怎么我竟然会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才知道,不是我们国学研究所邀请的。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新桃园大酒店的二楼餐厅,他已经在那里了,随行的还有两位,一位是东北某省一所专科学校的校长和她正在读书的大学生女儿。他们都是晓江的粉丝,追随晓江搞生命教育的。在那所学校里,也正在开设这种课程,这是晓江推广生命教育的客观成果之一。晓江在席间不断地夸赞我,说我学问做得好。我也一样夸赞晓江是创新型、开拓型的优秀学者。大约也只是说了一个多小时的闲话,九点多钟的时候我就离开了,晓江他们也稍事准备去了学校。我本想去捧捧场,顺便也听听他的讲座,但因确实有事缠身,没能去听他的演说。不知晓江当时的心里,是否感觉不快。
晓江很能讲,也很擅讲。讲起课来很有感召力,几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十分引人注目,有相当的震撼效应,我亲眼见到的。
最后一次见到晓江,是在2011年10月的厦门大学,缘由是厦大成立了一个国家级的周敦颐研究会,我和晓江都在会上被选为学会的理事。那一晚在喝酒的时候,晓江似乎先退了,但是起初谈得都很尽兴,晓江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不爽的感觉。此后,他还在通过手机短信给我发他很得意的顺口溜。去年过年时,我还真想着给他发个短信,客气客气,联系联系,给老兄拜个年,问问他近来的情况怎么样。可不知为什么就是没发出去。我从东北老家过年回来不久,就接到了景海峰教授悼念他的短信。
海峰兄的这个短信,当时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看到网上为数不多,但却无的放矢的相关说法,我忍不住替老朋友说几句话。
其实生死都是人生的常态,只是我们只能感受到生的状态,所以才会因为陌生而产生对死的恐惧和厌憎。热爱生命和热爱生活的意思自然可能包含了对生的事实本身的执泥,以为选择了死,就是不热爱生活,不珍惜生命。这是极端无知而且无聊的一种说法。晓江选择这样的方式离去,也是对生命的珍重,他有自己的生命所不能承受的重载,别人没有办法彻底了解,都是站在俗人的立场上妄加推断,乱加评判。对于晓江这种早已参透了生死的人来说,生和死是一样的,要么痛快的生,要么绝然的死。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难道就是因为他是研究生死学的,讲生命教育课程的老师,他就没有选择死的自由和权力了吗?他的死就是背弃自己的主张,就是背叛自己的理想吗?这根本就是毫无意义和根据的逻辑。晓江这个事情,使我感到要真正的改变世俗的成规和成见该有多么的困难。很多人受到了晓江热爱生命的教育,他们却不能理解晓江的选择,反而觉得受了晓江的欺骗!如此诬枉老师,怎么有资格作晓江的学生?晓江一生如果教出来的都是这样的学生,那可真是枉费了苦心!晓江是诚实的,他不会欺骗人。那些认为晓江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就是对他们的欺骗的学生和相识们,其实是真正地欺骗了晓江,从而也欺骗了自己。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真心跟晓江学习热爱生命,而只是想借助晓江的说法,为自己苟活于世间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根本的意义上,他们离晓江的距离太远,晓江还以为这么多人都在对他讲说的“热爱生命”感兴趣,动真心,刚好是被这些家伙欺骗和蒙蔽了。热爱生命的基本要义之一,就是要尊重生命,尊重生者对生与死选择的权力。选择的主动性本身,就是对生命的尊重,这份尊重表达的,正是对生命的由衷的热爱。如果不出于对生命的真正热爱,生存者是不会做出任何生和死的选择的,只是跟着肉体一路苟且的活着,行进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而已。“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诬枉和亵渎生命的哲学,这是行尸走肉的自白,不是对生命的真正热爱。如果什么都不选择,只是混混沌沌地混着活,生存者就不具有对生命的主动权,就不是生存的主体,就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而只能是看似被自己“拥有”的物质生命的附庸和奴婢。只要肉体生命还没结束,就可以依附在上面捡拾残羹冷炙,就可以借助物质生命的尚未泯灭,满足自己可怜的一点生存和享受的需求和欲望。如果把这种情况当成是尊重生命和热爱生命的话,那么生命就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尊重和热爱的了。
当然,我们绝不主张轻易舍弃生命。因为舍弃了生命,生活的事实也就就此结束了。那样的话,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实现理想、历练才干,就再也没有机会欣赏天地万物的和谐与冲突之美,再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受,同时让朋友和亲人分享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再也没有机会去展现由生命发出来的伟大力量和原本就归属于生命的崇高壮美。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生活,以便在生活的过程中认识生命、理解生命、成就生命。进而发挥生命的创造力,展现生命的光辉。但是,好好地活着,不是苟且地活着的意思。苟且的生活不是生活,只是苟活。苟活就是人家怎么活,自己就怎么活,生下来以后,好像什么都被安排好了,吃饭、睡觉、拉屎、尿尿,读书拿文凭,提职得薪水,赚钱买房子,发情找配偶,结婚生孩子。按照大多数人“规定”了的样子,了无自知自觉的行走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烦。不要理想,不求实现生命的价值,无视正义与否,不管天昏地暗,无情无义,不忠不信,总之就是一句话:只要活着就行。这跟猪有什么不同!猪要是这样,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责备,因为它天生就是这样,天生它也只让他能够这样。这就是伟大的王船山先生痛骂“庶民是流俗”,“流俗是禽兽”的根本理由。人不是这样,人要这样就不如猪。人是天地的精华,他要有不断向更高、更远追索的目标,他要借助承载生命的肉体前行,当他的肉体承载不起的时候,他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这本是无罪的,更不应该受到指责!
当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无一不因行走在世间,留下这样、那样的眷顾和依恋。选择自我了断,本来就万分的难忍,做出这种选择的人,内心世界里一定有他(或她)不得不这样选择的理由,如果不是因为某一件具体事情的刺激,而一时间失去理智的话。这样说来,他们似乎比生者更应该受到理解和尊重,而不是说三道四和妄加指责。而当他们走掉的时候,这些被暂时留在世间的生者们,也一定会感到难过。这是逝者在生时的活动,带来的自然回响,也是逝者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回响声息的大小,自然会因人而异,但只要是回响,就都是生命最美的壮歌,都是生命曾经闪亮的划过的痕迹,都是生命的伟大和光荣,都是生命不朽的成就和丰碑。
晓江是一颗流星,他闪亮地划过了,虽然他已暗淡地划过去了!